


从无人问津到走出撒哈拉——非洲法语文学的新视域
来源:本站 发布:2024-03-14 点击:1805
作者:刘成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一百多年来,非洲法语文学以其虚构的方式重构了殖民历史,对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社会不公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其特有的认知能力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表现非洲人的不幸命运,非洲黑人作家们希望写出一种具有“非洲范式”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表现黑人特有的审美取向,同时还有所创新,否则就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非洲文学。因此,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法语文学特别是口头文学的属性,需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当然,从“黑人特质”的视域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塞泽尔 资料图片

桑戈尔 资料图片

格里桑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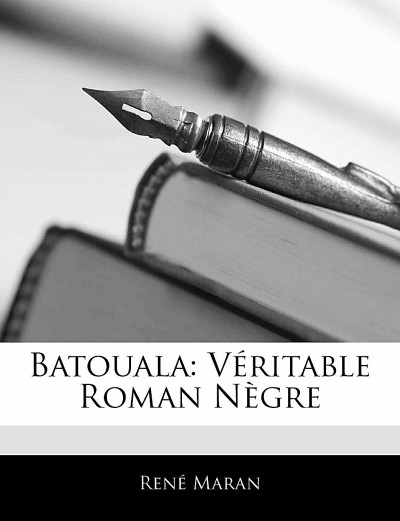
《巴图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说》封面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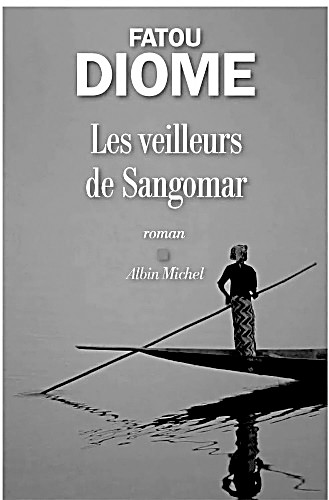
《桑戈马尔守夜者》封面 资料图片
1.主体意识的觉醒
1921年,加勒比地区的黑人作家勒内·马朗(1887—1960)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从此非洲法语文学正式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马朗生于南美洲的法属圭亚那,并不算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年少时,马朗在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接受法式教育,但常常有机会去父亲工作的非洲旅行。长大后,他在法属赤道非洲谋取了一个殖民地行政长官的职位。他的代表作《巴图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说》(1921)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情感经历丰富、拥有神奇的力量、战功显赫的黑人酋长巴图阿拉。通过对该人物的刻画,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法国殖民统治下非洲黑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法国殖民者的恶行,尤其是彼时法兰西所谓的“先进文化”对黑人世界所产生的巨大伤害。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1850—1923)早先曾写过一部有关非洲风情的小说,但是,真正把黑人作为小说主要人物来加以塑造的并不是洛蒂,马朗才是非洲法语文学当之无愧的鼻祖。在《巴图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说》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黑人,而且非洲元素十分丰富。马朗采用了一种并不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且尝试了他以前并不那么擅长的小说创作。值得注意的是,马朗并没有放弃非洲的文化传统,仍然保留了民族特有的表达形式。在当时,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具有独立意识的非洲精神,很快就遭到了法国当局的封杀。
不难看出,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觉醒意识成了非洲法语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在塞内加尔国父、诗人列奥波德·桑戈尔(1906-2001)看来,马朗是“黑人特质运动”(又译作“黑人性”“黑人精神”等)的先驱,因为他的文学创作引发了读者对非洲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也许,正是因为马朗有着法国和非洲的双重身份,法国才将龚古尔奖颁给了他。这不仅能够显示法国的“包容”,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存在主义作家萨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法国殖民统治者的眼里,这类具有抗争性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殖民教化过程中一些无足轻重的牢骚罢了,一个奖项并不能动摇法兰西帝国在非洲的根本地位。
过去,在许多法国作家的笔下,有关非洲题材的作品侧重描绘的是秀丽的风光、野蛮无知的土著人以及神秘愚昧的社会习俗,字里行间流露的是欧洲文化以及白人种族的优越性。20世纪30~40年代,桑戈尔等一批年轻学者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广大黑人民众。在他们的笔下,非洲不再是眼前现实的非洲,而更像是一个令人神往的美好世界。他们扛起反殖民主义大旗,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非洲法语文学逐渐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就非洲法语文学而言,“黑人特质”是一个颇具争议且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在《黑人精神:非洲文学的伦理》一文中,我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曾经指出,黑人精神是非洲诗人从事诗歌创作伦理价值的内核。桑戈尔将黑人的情绪与希腊人的理性进行对比,在竭力颂扬非洲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同时,深入阐释了对“黑人特质”内涵的理解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桑戈尔出版了诗歌选集《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萨特为这部诗集写了序,在序言中,他把黑人诗人形象地比喻为“黑人俄耳甫斯”。这个比喻可以被视为萨特对殖民主义情景中“黑人特质”的最本质的回答。有了这个序,“黑人特质”(主要在诗歌中)的定义经过不断界定,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可。
2.记忆成为永恒
非洲法语文学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特殊的文学类别。原始宗教、神话故事、巫术和祭典礼仪常常把读者带进一个神秘的世界。在第一代黑人小说家的笔下,格言、警句、歌曲、名言、箴言比比皆是,举不胜举。非洲法语文学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鼓声和歌舞声营造着一种特殊的氛围,为非洲法语文学平添了一种活力四射的动态形象。尽管黑人的文化传统及其内在的精神属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毋庸置疑,其特点和表征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被加工和提炼出来的。在黑人小说家的心目中,如果说欧洲人是“理性的”,那么非洲人便是“感性的”;如果说欧洲是一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工业社会,那么非洲就是一个充满和谐和幸福、天人合一的人间天堂。他们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黑人同胞才能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不同于白人的价值理念中找到自信和尊严。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伊(1928-1980)就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小说《黑孩子》的故事发生于1933~1948年,那时几内亚还没有独立。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巴巴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父亲的神奇炼金术和母亲神秘的通灵术。莱伊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在他的笔下,小说中的场面无不生动有趣。
通常,文学虚构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构,文学能够唤醒人们的记忆,通过纷繁复杂的爱与恨能够让记忆更加刻骨铭心。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告诉我们:“文学无法改变世界,但文学可以挑战真实,将真实化为美”。毛里求斯法语作家达维娜·伊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小说《苦难》(2020)为我们生动描绘了毛里求斯民族独立后仍处于殖民阴影下的乡村生活。主人公是个沉默寡言的弃儿,他唯一能说的一个词语就是“苦难”。后来,有个名叫阿尔琼的小伙子心生悲悯,收留了他。他们俩相依为命,音乐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奇特的交流方式。伊托曾在法国生活十多年,回到毛里求斯后开始文学创作。故事的发生地就是他的故乡,但是,这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远远超出了他生活的那个小城,饱含着对祖国毛里求斯深情的爱。
2003年,塞内加尔女作家法图·迪奥梅凭借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大西洋的肚子》进入了读者的视野。这部小说后来被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2006~2019年间,她又陆续出版了《凯塔拉》《我们未完成的生活》等作品。相对于斩获各类国际大奖的非洲作家,迪奥梅的名字在我国相对陌生。但是,作为新锐作家,迪奥梅是我们了解非洲法语文学不可忽视的存在。2021年,她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桑戈马尔守夜者》。这部小说在继承非洲文学传统的同时,重点描绘了非洲女性的生存状况。作者以2002年“乔拉号”沉船事故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库姆巴在丧夫之后,通过写作来重建个人生活的经历。“暴风雨摧毁了她的一切,而她把风暴关进了日记本里。”这是《桑戈马尔守夜者》中一句令人记忆深刻的话,也是这部小说的灵魂。
3.戏仿民间传说
与马朗、莱伊、伊托、迪奥梅等作家一样,喀麦隆作家阿兰·马邦库也是个说故事的能手。1966年,马邦库生于刚果(布)黑角市,拥有法国和刚果(布)双重国籍,现定居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毫不夸张地说,马邦库是法语世界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国最负盛名的非裔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打碎的杯子》《豪猪回忆录》《明天,我二十岁》《黑角之光》等。马邦库22岁时曾在法国求学,1998年发表小说处女作《蓝-白-红》并一举获得当年的“黑非洲文学大奖”。他的作品多次荣获法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并被译为英、西、葡、意、韩等多国文字。2012年,他的作品被授予法兰西学院亨利·加尔文学奖,也曾入围2015年布克国际奖终选名单。2021年11月,他荣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2022年担任布克奖的评委。
在《豪猪回忆录》这部小说中,叙事者是一只非洲豪猪,但这不是一头平平无奇的野兽。白天它在丛林里与同伴们撒欢,晚上暴露出来另一个身份,成为黑人小男孩奇邦迪的附体。表面上看,这是一只豪猪的故事,但读者很快就会发现,马邦库实际想要表现的是非洲的社会现实。在这个故事里,马邦库让动物成了叙事的主体,并且具有了人一样的性格特征。动物附体的故事设定源于非洲民间传说,“讲故事”的形式也来自非洲口头文学的传统。因此,这部具有泛灵论气息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非洲本土文学色彩。在这个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里,动物成了体察世界的主体,而愚蠢自大的人类则成了动物调侃的对象。
成为附体之后,那头勇敢快活的豪猪离开了自己的伙伴,尽管有时它并非心甘情愿,但是,它不得不听从主人的吩咐,用身上的刺去伤害他人。整部小说都是豪猪以独白的口吻向猴面包树倾诉心声,讲述自己的不幸命运是如何与一个男孩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成了“邪恶附体”,豪猪不仅能听懂人话,而且有了人一样的阅读能力,因而在讲述痛苦经历的同时,也抒发了一连串对人类及其文明的长篇大论。这为整部小说增添了一种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效果。在非洲的生态系统日益遭遇荼毒的今天,将人与动物进行倒置,无疑具有一种警世的味道。正如豪猪所说:“人类并不是唯一能思考的动物。”在这部小说中,马邦库借助于传统的非洲民间传说并进行戏仿,让读者领略了独特的讽刺艺术和文学想象。
4.话语权与文化身份
相对说来,非洲法语文学在我国读者中较为陌生。一方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没有文字记载的传统,早期的文学主要是口口相传的英雄史诗。例如,古马里史诗《松迪亚塔》、索宁凯族史诗《盖西姆瑞的琴诗》以及刚果伊昂加族史诗《姆温都史诗》。直至20世纪中后期,这些作品才被整理出来正式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这些作品终于让人们领略到了非洲法语区各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世界文学史的话语权一直被西方人操控,似乎非洲人在文学创作上有先天的缺陷,根本不能与西方作家平起平坐。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大陆与非洲大陆之间阻隔的不仅仅是地中海,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之间还阻隔着一道肉眼看不见的、无法逾越的思想鸿沟。在这条鸿沟中,殖民主义犹如一个可怕的幽灵,给非洲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创伤至今仍无法愈合。
非洲法语作家早就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试图终结文学创作上的附庸地位,而且坚信这个愿望将来有一天最终能够实现。他们希望把本民族的历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的创作引发了有关“文化身份”“去殖民”“文化多元”“后殖民主义”等诸多话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法语文学的兴起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第三世界的文学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在推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黑人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用“黑人特质”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消解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荒谬论调,为纷繁复杂的后殖民时代提供了一盏又一盏明灯。尽管作家们的创作倾向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法国文艺理论家德勒兹所说的“少数文学”早已不再是边缘文学。
5.不容小觑的加勒比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非洲法语文学而言,加勒比法语文学举足轻重,因为那里的人绝大部分是非洲人的后裔。著名的作家有塞泽尔(1913-2008)、法农(1925-1961)、格里桑(1928-2011)、孔戴(1937-)等。其中,塞泽尔堪称最为杰出的代表。20世纪30年代,他在巴黎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朋友一道发起了“黑人特质”运动,从此走上文学之路。他用充满非洲意向的法语语言,表达了强烈的叛逆精神。塞泽尔一生创作颇丰,其代表作是长篇散文诗《还乡笔记》。应该说,他的所有创作似乎都立足于他的民族情怀以及“黑人特质”思想。毫不夸张地说,黑人之美、黑色之美都成了他讴歌的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塞泽尔开始创作戏剧。通过改写莎翁的《暴风雨》,通过颠覆剧作中心人物的主仆关系,塞泽尔以大众化的戏剧艺术形式生动地表达了后殖民主义思想。
作为塞泽尔思想的继承人,格里桑善于把“文化身份”的思考融入小说的故事。格里桑不仅是个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个举世瞩目的思想家。从加勒比社会现实出发,格里桑提出了一种基于语言和文化关联的世界观。在格里桑的眼里,文化与语言之间永恒的、相互渗透性的运动推动着文化全球化进程。这种全球化能将遥远的、异质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能产生超乎人们想象的效果。格里桑的哲学思想是塞泽尔“黑人特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审视了不同文化的杂糅性及其本质。在格里桑的心目中,“克里奥尔化”并不是加勒比海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格里桑的“多元世界”强调的不是文化的清一色,而是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和包容,尤其是当今边缘文化的前途和命运。他先后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术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相辅相成,以各自的思想火花照亮了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21世纪以来,非洲法语文学的出版、翻译与传播在世界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过去无人问津的非洲法语文学成功地走出撒哈拉大沙漠,成了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马朗、桑戈尔、塞泽尔、莱伊、伊托、迪奥梅、马邦库等一大批黑人作家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非洲知识分子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去殖民化过程中的责任与历史担当。涵盖主体意识、民族意识、文化身份的“黑人特质”是我们了解和把握非洲法语文学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4日 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类型:转载
附件:


